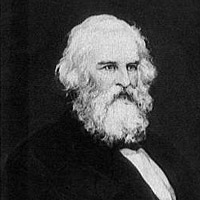
亨利‧沃茲沃恩‧朗費羅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1807-82)
生於緬因州的波特蘭,在博多因大學讀書,與霍桑同班。一八二六至二九年在法國、西班牙、義大利和德國旅行。回國後任博多因大學近代語言學教授,直到一八三五年。是年再赴歐洲,返國後繼蒂克納出任哈佛大學法文及西班牙文教授。隨後因不滿教書生涯,一八五四年辭去教授職位,專心致志於文學。那時他已以下列詩文作品蜚聲國際:《海皮里昂》(Hyperion,
1839),《夜吟》(Voices of the Night, 1839),《西班牙學生》(The Spanish Student,
1843)和《伊凡吉林》(Evangeline, 1847)。《海華沙之歌》(Hiawatha, 1855),《邁爾斯。斯坦狄什的求婚》(The
Courtship of Miles Standish, 1858)與若干後期作品出版後,聲譽日隆。他兩次結婚,兩個妻子都在悲慘的境遇中去世。
詹姆斯‧拉塞爾‧洛威爾 (James Russell Lowell, 1819-91)
生於麻塞諸塞州的坎布裡奇。哈佛大學畢業。一八四四年娶熱心社會改革的瑪麗亞.懷特為妻,在她的影響之下,寫了多篇反對奴隸制度的文章。早年以《寫給批評家的寓言》(A
Fable for Critics)和《比格羅詩稿》(Biglow Papers)初集(兩者均於一八四八年出版),知名於世。瑪麗亞‧洛威爾死於一八五三年,此後他對於改革的興趣逐漸降低。一八五五年繼朗費羅之後任哈佛教授,數年後開始大量寫詩與散文。他是《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的首任編輯,也曾為《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工作。一八七七至八○年任美國駐西班牙公使,一八八○年至八五年任美國駐英公使。
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1809-94)
生於麻塞諸塞州的坎布裡奇。哈佛大學畢業。曾去法國學醫,返國在達特默思執教後,於一八四七年出任哈佛解剖學及生理學教授,直到一八八二年。在波士頓與坎布裡奇文化及社交活動中聲名卓著。起初以善講故事與寫詩在國內為人見重,隨著《早餐桌上的霸王》(The
Autocrat of the Breakfast-Table, 1858),《早餐桌上的教授》(The Professor at the
Breakfast-Table, 1860),《早餐桌上的詩人》(The Poet at the Breakfast-Table,
1872)以及其他著作的陸續出版,其中包括三部小說和幾本詩集,使他的名聲也傳到了國外。其子小霍姆斯,亦為哈佛傑出人物,聲譽不在乃父之下。
威廉‧希克林‧普雷斯科持 (William Hickling Prescott, 1796-1859)
生於麻塞諸塞州塞勒姆鎮。哈佛大學畢業。一八一五至一七年在歐洲旅行,開始致力於歷史研究。其嘔心傑作《費迪南德與伊莎貝拉史》(三卷,History of
Ferdinand and Isabella, 1838)出版後一舉成名── 朗費羅說他是"一個顯著的例子,恆心與毅力可使人大有成就"。繼而著手編寫《墨西哥征服史》(三卷,History
of the Conquest of Mexico, 1843),跟著又出版《征服秘魯》(兩卷,Conquest of Peru,
1847)。去世時出版了三卷《菲利普二世傳》。
約翰‧洛思羅普‧莫特利 (John Lothrop Motley, 1814-77)
生於波士頓,哈佛大學畢業。在德國進修兩年後回波士頓攻讀法律。寫成兩部小說《莫頓的希望》(Morton's Hope, 1839)與《快樂山》(Merry
Mount, 1849)。開始研究荷蘭史。結果出版了《荷蘭共和國的興起》(三卷,The Rise of the Dutch Republic,
l 856),《統一尼德蘭史》(四卷,History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 1860,1867),與《巴內韋爾德的約翰傳》(二卷,Life
and Death of John of Barneveld, 1874)。一八六一至六七年出任美國駐奧地利公使。一八六九至七○任駐英公使。旋被召返國,但並非由於他的過錯。
弗朗西斯‧帕克曼(Francis Parkman, 1823-93)
生於波士頓。哈佛大學畢業。一八四三年到四四年在歐洲旅行,一八四六年到美國西部旅行,過分的勞累損害了他的健康,不過也使他寫成了《草原千里》(Oregon
Trail, 1849)。儘管健康情況惡劣,他還是專心致志於編寫一系列的英法在殖民地美洲鬥爭史。《龐提亞克謀反始末》(History of
the Conspiracy of Pontiac)首先於一八五一年出版。經過一段時間休息以後,又出版了《法國在新世界的拓荒者》(Pioneers
of France in the New World, 1865),其後繼續寫足了六卷,以《半個世紀的衝突》(A Half-Century
of Conflict, 1892)結束。他也寫過一部小說《家臣莫頓》(Vassall Morton, 1856)和一部關於園藝的書,他在哈佛還當過園藝學教授。
第六章
其他新英格蘭作家
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內戰過後那幾年裏,如果問起美國當時的大作家有誰,很少人會提到梅爾維爾和惠特曼的。他們一定會提到愛默生,說不定還會提到教友會詩人惠蒂埃,兩個都是麻省人。然而地域觀念會使他們想到上面所列的那些人:他們不僅和麻省有關,而且和波士頓(與坐落在附近的坎布裡奇的哈佛大學)有關。他們的聲譽,在他們那個時代,實在大得驚人:像朗費羅的《生命頌》('Psalm of Life')那首詩,波德萊爾對它非常熟悉(這我們可以在他的十四行詩"Le Guignon"裏看到),一個在克里米亞作戰的英國士兵對它也一樣熟悉,有人聽見那個士兵在塞瓦斯托波爾臨死以前背誦《生命頌》中的句子。
今天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了。即使我們對那幾個文學家還存有敬意,他們的著作(可能帕克曼的除外)已不再受到廣泛的閱讀。那些名噪一時的詩人,在今天的教科書裏,已被毫不客氣地擠在一起,列為短短的一章。不管是史家還是詩人,全都黯然無光,連明智派和非明智派都比不上了。愛默生不是在他的日記(一八四一年十月)裏說過"國家街對於超驗論的看法是,它可以使合同失效嗎"? 幾年以後他又在日記裏寫道:
如果蘇格拉底在此地,我們可以去找他同他交談;至於朗費羅,我們就不能找他和他攀談;他那裏是一所宮殿,奴僕成群,美酒羅列,衣飾華麗。
朗費羅不是在一八四O年十二月也寫過"整個坎布裡奇如今只剩下一個超驗論者了──而他只不過是個助教!在神學院一位也沒有了;那班受影響的,一去不返了"這樣看來,我們看到的不是康考德單純的世界,倒有一點像惠特曼幻想中的坦尼森時代的英國。那是一個商人或紳士派文人充斥的波士頓(紳士派這個詞是紳士之一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首先採用的)。這些紳士們生下來就有一根銀羹匙從嘴裏伸了出來,一般是在哈佛讀書(或者是教書,通常是讀了又教),討厭民主和邊遠地方,也討厭當代問題;他們都只向歐洲和往事中去尋求慰藉;對於他們的時代和國家則了無所知;他們過於文雅了。
這樣的指責川流不息,正如佛農‧巴靈頓所施加於紳士派文人身上的那樣。巴靈頓的"傑斐遜主義"傾向是人所共知的,不過有那麼多美國學者同意他的看法,以至使攻擊這派文人成為當今美國一種全國性的娛樂了。說是娛樂其實也沒有什麼好玩的,過去把他們捧得太高,如今又成了坐待攻擊的目標。這種遊戲一直受人歡迎,一定還有別的原因。就是紳士派這個觀念──正是這觀念!──和這件事有點關係!我們在前面說過,美國缺少一個自信的保守主義的傳統,紳士這個字成了受人詛咒的名詞,意思和勢利鬼不相上下。對於非波士頓的美國人來說,紳士派文人不僅勢利眼,而且心地偏狹,過於沾沾自喜,在精神上太過奉承英國(格威爾和莫特利還做過駐英公使)。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帕蒂教授說得不無道理:巴萊特‧溫德爾的《美國文學史》,實在應該改名為《哈佛大學文學史兼論美國次要作家》。到了一九○○年,這類強調性的著作開始顯得有些荒謬可笑了;這些著作使非波士頓人看了生氣,倒不是因為它們荒謬,而是因為它們寫的大部分都很真實。波士頓在十九世紀大半時期是美國的文化中心。第一流的文人都聚集在那裏或是鄰近的新英格蘭地區。它有良好的出版社,和出色的刊物──《北美評論》創辦於一八一五年,《大西洋月刊》創辦於一八五七年。只有波士頓──坎布裡奇勉強可以和遙遠的英國文化中心牛津或康橋相比;也只有在波士頓你才可以舉出一些名門世家(如諾頓、洛威爾、亞當斯、霍姆斯、洛奇等家族)值得和比如說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特裡維廉、赫胥黎、韋奇伍德和斯蒂芬斯等望族相提並論。《大西洋月刊》登載的文章有一大部分出自波士頓文人之手:愛默生在一八六八年講過一個故事,"一次,大西洋俱樂部開會時,有人把《大西洋》新出的一期送了若幹份進來,每人搶著站起來拿了一本,個個坐下去捧讀自己的文章"。我們可能認為這是典型波士頓人的個性。不過《大西洋月刊》編輯除了向波土頓還能向那裏去徵稿呢?《大西洋月刊》刊載了蒙威爾斯的處女作,一首詩;它選用了朱厄特一篇小說的故事,那年她才十九歲;他們把園地開放給年輕的亨利‧詹姆斯,也開放給馬克‧吐溫。如果說他冷落了梅爾維爾和惠特曼,其他的美國雜誌,也幾乎莫不如此。除此以外,在內戰以後那幾年,美國的雜誌只要是美國作家文章就照登不誤,但好的實在不多。事實上波士頓是個使人惱火的目標。在美國它最像一座學院,然而它沒有學院這兩個字使人聯想到的那麼反動那樣麻木不仁。許多對於它的攻擊,包括巴靈頓的攻擊在內,都是不公平的,而且還有點時好時壞,譬如說,巴靈頓對於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的缺點一味攻擊不肯放鬆的時候,他反而把霍寫成既可愛又風趣的人物了。
反對波士頓的人們有一個難處,他們的敵人善於先發制人,解除他們的武裝。波士頓人深知自己的缺點。晚一代的亨利‧亞當斯替一八二○年到七○年的作家辯護道:
上帝知道我們多麼瞭解自己缺乏知識! 對於自己缺少信任會促使自己自省──神經質的自覺──內心煩躁地不喜歡美國,憎恨波上頓。……我們都是些半生不熟的歐洲人──皇天在上──我們多麼單薄呵!
對方做了這樣的懺悔,你怎麼能夠還說他"自鳴得意"呢? 況且,紳士派文人雖然一般說來都是富有的人,可是他們在意向上並不輕浮。像巴靈頓所承認的,他們十分勤奮,甚至從小就很勤奮。雖然朗費羅能夠在哈佛大學當上現代語言教授是出於幸運,他謹慎施教,對於這個職位是勝任的。如果說他不是一個偉大的學者,那他也是個有教養的人,對幾種文字涉獵甚廣,並能在相當程度上運用。接替他出任這個教職的洛威爾也極其稱職。霍姆斯是個有本事的醫生,他在哈佛醫學院做了三十五年的解剖學教授。普雷斯科特、莫特利和帕克曼這三位史學家,都有遠大的抱負,而且都已盡力完成了他們的計劃。事實上,紳士派文化抵抗了懶惰的誘惑,其英勇處並不亞於他們的祖先躲開魔鬼的陷阱。普雷斯科特和帕克曼,由於視力衰弱,嚴重影響了工作,可是他們和別人一樣,當得起朗費羅在《生命頌》中所描繪的崇高情操:
以一顆承受任何命運的心
讓我們起立而行:
不斷成就,不斷追求,
學會埋頭苦幹和耐心等待。
指責紳士派文人過於文雅,其實也並非完全得當。批評家們喜歡攻擊他們在飲食上過於揮霍,彼此互相標榜,還拿他們文學上的細膩作風和馬克‧吐溫與惠特曼豪放的風格相對比。人們時常提到馬克‧吐溫在波士頓一個晚宴上所受到的冷 落,當時他是想善意地開朗費羅、愛默生和惠蒂埃的玩笑。但是這個對比雖然在某些方面說得不錯,卻也不能過分誇張。洛威爾徹頭徹尾是個紳士派,就曾以他的方言寫成了《比格羅詩稿》,成為美國"本土"文學一個重要的範例。鼓勵印第安那州小說家愛德華‧埃格爾斯頓描寫荒涼的山林地帶移民生活的就是洛威爾。朗費羅有時也寫得強健有力,例如在他的小說《卡瓦納》(Kavanagh)中,描寫屠夫威爾默丁斯到達新英格蘭一個村莊的情景:
屠夫威爾默丁斯先生站在車子旁邊,有五隻貓環繞著他。……威爾默丁斯先生每天不僅供給這個村子新鮮的肉食,他還秤過莊上所有的嬰兒。幾乎沒有一個嬰兒不曾用絲巾裹著在他的提秤下面吊過。……他新近娶了一個女帽商,她賣的是鄧斯特布林十一辮透雕細工彩色草帽,他們的蜜月旅行是到鄰近一個城鎮去看一個謀害妻室的人接受絞刑。一對巨大的牛角,分開掛在他屠宰房的三角牆上,屠宰房旁邊有幾個制革的大坑,小學生們認為大坑裏完全是血!
或者,讓我們來提一提一切都和霍姆斯相反的馬克‧吐溫吧,霍姆斯在一八六一年出版過一部小說《艾爾西‧文納》(Elsie Venner)。在這本小說裏,男主人公為了自衛,一腳把一條野狗踢了出去。
它像包裹似的從學校敞開的大門裏跑了出去,發出極其可憐的哀號,它那半截尾巴緊貼在身後,緊得像它的主人把大折刀粗短的刀刃折疊起來那樣。
在馬克‧吐溫的《湯姆‧索亞歷險記》(Tom Sawyer, 1876)裏,有一條捲毛狗在教堂做禮拜的時候蹲到一條甲蟲身上,"慌忙逃上教堂座位中間的走道"。這段描寫最初後面還接續著"尾巴夾在腿中間像個紡錘",不過馬克‧吐溫的朋友兼顧問豪威爾斯為這句話在底稿邊緣空白上寫道:"好得很,只是有點不雅"。這句惹厭的話被刪去了;就是豪威爾斯沒有挑剔,馬克‧吐溫自己也可能把它拿掉的,因為他在講究"風雅"方面比起紳士派人來有過之無不及。
總而言之,巴靈頓關於紳士派文人之只在吹毛求疵、沒有美國氣派的說法是歪曲的,即使我們接受巴靈頓的某些批評標準,我們也不能只一味責備紳士派文人而不去責備別的許多作家。他們之中雖然沒有一個是徹底的廢奴主義者,但是他們也非常關心這場鬥爭的結果。朗費羅在日記裏讚揚過那個無法無天的約翰.布朗: 他和霍姆斯都有兒子在內戰中受傷。至於說到"本土"文學,甚至不喜歡群眾的帕克曼,也推祟過像《大衛‧克羅克特傳》和《阿肯色的大熊》等富有本國色彩的作品,他說這些著作都是"來自沒有受過教育的人民,或者是為了迎合他們而寫的",反過來說,。在那些比較高雅的作品裏,我們看到的只是優雅的文體,很少看到獨創的思想,這樣的文章很容易讓人認為是英國人寫的而不是美國人寫的"。
但是,為了替紳士派文人洗脫罪名,我們也有犯錯誤的危險,有可能走向巴靈頓的反面。老實說,就這派的詩人而論,他們的作品很少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話雖如此,我們也不能把這種貧乏完全歸罪於波士頓。難道詩人的不合時宜,在十九世紀的英國,不是和在美國幾乎同樣顯著嗎? 朗費羅、洛威爾與霍姆斯在英國很受歡迎,並非因為他們有意用不是美國的方式寫詩,而是因為他們對於詩的看法,和英國以及美國的高級人物對於詩的看法十分接近的緣故。像坦尼森這樣的人,與時代脫節,表現在他的詩和他的行為之間有鴻溝:他的詩寫得非常文雅,而他的生活卻粗鄙地填滿了煙草、啤酒和粗語。這並不是說坦尼森或紳士派文人都為了不能像說話那樣寫文章而發起愁來,請問又有哪個文人能夠像說話那樣寫文章呢? 然而就紳士派文人而論,他們碰到我們在第二章約略談到的那種麻煩,文雅的辭句和一般用語對於他們都不怎麼合適。我們可以這樣說,這是一個全國性的問題:波士頓的特別困難也許在於他們新英格蘭一本正經的傳統,使他們過分文雅。在這一點上,我們同意巴靈頓的看法,紳士派文人留給我們的整個印象是過於精美:這是當時英美的共同缺點,再加上波士頓特有的精細,使得紳士派詩人在他們的那個時代曾風行一時,但在我們這個時代裏卻不能流傳。
他們中最成功的文人是朗費羅,可是他又給我們提供了一些什麼呢?散文有《海皮里昂》與《卡瓦納》之類的浮淺小說,除了偶爾有些有意思的常識以外,在整體上矯揉造作得很。在詩歌方面,他留下了大量作品,從短歌到抱負不凡的巨作:《伊凡吉林》,《海華沙之歌》和但丁的英文翻譯。愛倫‧坡和惠特曼兩個人都有保留地說過,朗費羅有豐富的才能,可是他的詩沒有韻味,因為詩中的含意已由辭彙和韻律囊括盡了。和他相反,梅爾維爾在技巧上是個最拙劣的外行詩人,可是詩的內蘊卻要深厚得多。朗費羅也不是缺乏獨創性,不過才華不大。他在歐洲文學的閣樓裏忙著翻箱倒籠,找到了不少有趣的東西。和歐文一樣,他盡其所能給美國提供本國的民俗。他在一八四○年一月寫道:
我已經開闢了一個新的園地民謠,從《金星號遇難》開始,這條帆船兩周以前在暴風雨中在諾曼愁地方觸礁。……我想我還要多寫一點。美國民謠在新英格蘭這裏還是一塊處女地;有的是上等的資料。
他的確寫了許多,結果非常滿意:舉一個例子,很少有美國學生沒有讀過《保羅‧裡維爾的夜奔》的。可是他對美國的民謠並沒有真正的興趣;當時人們對於是否需要一種美國文學爭論不休,他覺得好笑,也表示懷疑。問題不是美國和歐洲孰輕孰重,而是"我的理想的詩的世界,還是外面實在的散文世界"。我們從那段引自《卡瓦納》的文章,可以看到他對散文也有興趣。不過他更喜歡寫詩,不管他寫的是歐洲還是美國,他並不怎麼想去追求真實。他從未去過美國西部,他看不出有去西部的必要(以他的條件而論,誰也不能怪他)。當他在《伊凡吉林》中想描寫密西西比河時,他只是走去看看班瓦德的密西西比河全景油畫就已心滿意足,那幅畫那時正巧在附近展覽。《海華沙之歌》的素材,取自斯庫爾貞拉夫特的和別人的作品,那首詩的韻律,來自芬蘭,雖然有人對那種韻律提出不利的批評,他還是固執使用。他在《我逝去的青春》中寫他的童年,他對於緬因州波特蘭的回憶,是由但丁的詩句引起的。"Siede la terra dove nato fui/Sulla marina",成了"時常我想起那個美麗的鎮子/那個坐落在海邊的鎮子"。還有那詩中的疊句:
男童的意志是風的意志,
少年的思想是悠長、悠長的思想──
來自赫德譯成德文的一首拉普蘭歌:
青年的希冀是風的希冀
少年的思想是悠長的思想
像這樣改編別人的作品本來沒有什麼不對,對於某些近代詩人,這是一種天賜的機緣。不過就龐德和艾略特而論,改寫(甚至直接引用)是為了要取得聯想的效果,而在朗費羅,則彷彿是他文學雜碎堆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通常讀者並不覺得那是借來的東西、縱然如此,也還是可以聞到來自朗費羅的一種輕微的雜燴的味道。比如在《海華沙之歌》裏,他筆下的印第安人顯得不真實,不是因為他沒有見過真正的紅印第安人,而是因為他們不是出自創作的想像,而出自浪漫的想像。因此,他們往往因為"過時"而顯得可笑,就像過了時的時裝圖樣一樣。模仿別人的詩文,把上邊這些文人淹沒了,可是它沒有能夠掩沒像惠特曼那樣的詩人:
他殺了高貴的穆喬奇維斯。
用皮給他做了一副手套
做的時候把有毛的一面放在裏面,
把裏面的皮面放在外面。
時間對朗費羅是無情的,不是由於他紳士派文人的作風,而是因為他只能滿足他那一代的需要,而不能超越這些需要。正如愛默生用他那有禮貌的鋒利的筆談到《海華沙之歌》:"讀你的作品永遠給我一種最高的滿足-我有安全感。我讀過各種各樣的巧妙的作品,不過最重要的是使我能夠感到安全的作品。"
洛威爾也退色了。但是並不是所有的作品都已失去光彩。《寫給批評家的寓言》(1848)對當時的美國文人,就曾說過一些機智而聰明的話,比如他說惠蒂埃:
滿腔熱忱不能分辨
單純的興奮和純潔的靈感
(還有批評他自己的那些話,因為按照典型的新英格蘭作風,人人都是自己最好的批評者。)《比格羅詩稿》中有些部分由於內容對於人類有機警、憤怒和幽默的批評,所以現在仍能保持不敗。有些文學論文寫得很好──例如討論喬叟和愛默生的文章──其中大部仍然可讀。他的作品十分流暢,措辭巧妙。詩文中有的是簡潔的短句,讀來清新可喜──
[華茲華斯]是華茲華斯郡的歷史學家
[梭羅〕注視自然像個謹守崗位的警探
雖然它們往往經不起進一步的審查。到了晚年,他成了美國最顯赫的文人,牛津大學請他去教書,他是艾德琳‧斯蒂芬(後來以佛吉尼亞‧伍爾夫的筆名聞名於世)的教父。
今天,他所以受人注意──可說特別受人注意──主要是因為他的一生可以說明美國文學的各個方面。年輕時,他熱烈信仰民主,主張廢奴。到了壯年,任哈佛大學的教授,也協助過《大西洋月刊》和《北美評論》的編輯工作。晚年他似乎保守起來了,成了一個紳士派的文人,他可以寫信給亨利‧詹姆斯,這樣說道:"我見過的最好的社會,總的說來是麻塞諸塞州的坎布裡奇。"他瞧不起惠特曼,對於華茲華斯"未能及早學習古典文學的優雅"深感惋惜。"正是這種優雅使蘭道的無韻詩那樣肅穆莊嚴,那樣強健有力……而華茲華斯從未到達這個高度。"作為一個有教養的紳士,洛威爾喜歡四海一家的感情。他對於歐洲的著名作家最為熟悉,就像他熟悉歐洲最好的旅館和最好的地方佳餚一樣,他的詩文滿是文學典故。他覺得建立美國本國文學的念頭非常可笑,朗費羅也有這種想法;比如說他用這樣的話諷刺過美國二流詩人詹姆斯‧珀西瓦爾:
如果涓涓細流如阿馮河能夠產生莎士比亞,雄壯的密西西比河該孕育出多麼偉大的巨人來呵!地理形勢第一次發揮了它正當的作用,成為第十個富有啟迪性的繆司女神。
但是作為一個美國人,洛威爾從不懷疑他的國家能對別人有所貢獻。他在內戰中寫的《比格羅詩稿》二集,對約翰牛說話的口氣,可沒有一點親英的味道:
何必誇誇其談,約翰,
把榮譽說得天花亂墜,
你根本不把它放在眼裏,約翰,
看它不值一個小錢?
在他的《外國人的某種謙遜》一文裏,他清清楚楚說他是個美國人,雖然他引用起歐洲文學的章句來易如反掌。事實上,像若干其他紳士派文人(像他以前的庫珀)一樣,他不得不向本國同胞為出身教養辯護,對歐洲人為本國比較粗獷的性格辯護。年事漸長之後,他加入了霍姆斯等人的紳士派文人行列,他們相信波士頓─坎布裡奇是新舊兩個世界最好的東西薈萃的地方。但是作為一個作家,他對於雙方都沒有充分領略到,因之也從未找到完美的表達方式,比如說,他在《梅森和斯賴德:一首揚基牧歌》裏寫道:
陌生的新世界呵,它從來沒有年輕過,
逼人的需要把青春從你那裏搶去了,
森林裏褐色的棄兒,他的小床周圍,
有印第安人劈啪的腳步聲踱來踱去……
這幾行詩是由一首較早的詩《聲音的力量:一篇有韻的講演》改寫而成,原句是:
陌生的新世界呵,從來沒有年輕過,
殘暴的需要把青春從你那裏搶去,
森林裏褐色的棄兒,張著乾癟的眼睛
千年百代的孤兒和繼承者。……
兩節詩哪一節好?很難說。前面用方言寫的那一節比較隨便,逼人的比殘暴的更加有力,然而用方言寫總有些格格不入。印第安人劈啪的腳步聲改得並不好,整個看來,用方言寫的詩聽起來總有些牽強。說話的人過了一會不用方言了,文雅地提到"屬於海的鬃毛",又趕快回到方言上來。兩節詩都很巧妙,但是都沒有力量。另外的紳士派文人,同樣也都有雙重性格,只是比較不大明顯而已。我們選擇其中一個,歷史學家普雷斯科特。他的父親、祖父和曾祖父都住過他在哈佛的那個房間,家用食具上都刻有盾形勳章;他的風格和英國人沒有兩樣,可是他並非英國人──他是一個紳士派文人,看到英國的風景會使他想念"粗糙的籬笆,一個老樹樁……從那裏可以看到大自然的頭並沒有經人的手用力爬梳過。我覺得我不是在自己親愛的荒涼的美國。"
如果洛威爾才華較高,他說不定可以克服"婆羅門"派文人的風格給他帶來的障礙。按照他的實際情形──說不定從上面所引的書裏可以看到一個苗頭──寫詩對他來說太容易了。一節一節寫下去,他那顆靈巧的心還是沒有把主題說完。他那首大受讚揚的《哈佛紀念會上朗誦的頌歌》,過分典雅,措詞過於巧妙,也寫得太長了些。詩句非常典雅,但其中所寫的痛苦與勝利,寫得過於明顯。洛威爾知道他這個毛病;差不多在二十年前他寫信給朗費羅說,《寫給批評家的寓言》完成後,一段時期內他將放棄寫詩,因為他不能"慢慢地寫"。
一般地講,洛威爾的朋友霍姆斯也有同樣的毛病,他寫起詩來也毫不費力,對於語言和方言問題極有興趣,熱愛雙關語和警句,並且認為自已是個紳士。此外,他也是個科學家:他寫過一篇有關產褥熱的重要論文,以他這個身份,他有一點鄙視浪漫主義的想法。他最喜愛的詩人是波普、戈德史密斯和坎貝爾;他們那個時代直率文雅的作風頗使他嚮往。他把"神秘主義"當做譴責之詞來使用。他說,"有想像力的作家追求的是效果,科學家追求的是真實。"這並不是說他不容一點想像,他認為想像應該是附屬於科學的幻想。他筆下的霸主說道,"生命是靠呼吸氧氣和情感來維持的。"他的作品正是這樣的混合記錄。他一方面偶爾寫點詩為茶餘酒後或校友聚會助興,有時說點俏皮話("整個愛的藝術可以在百科全書中'築城"──'fortification'──項下找到");另一方面,他很喜歡把科學發現應用到人類行為上面。因之在他的小說《艾爾西‧文納》(Elsie Vnner)、《守護天使》(The Guardian Angel)和《致命的反感》(A Mortal Antipathy)裏,他把輕鬆的地方色彩摻入可能具有重大意義的主題:所有這些小說裏的人物,對他們的行為到底應該負多少責任為艾爾西‧文納是個壞人,不過她的邪惡是由於遺傳(正如霍桑的短篇故事,邪惡莫名其妙地來自進入母親血液中的響尾蛇毒),所以不應對她的行為負責。另外那兩部小說的主人公,他們的行為同樣也已前定。這樣說來,我們應該為我們的行為負責嗎?社會應該懲罰我們嗎?這樣的懷疑,加上社會是虛偽的想法,使十九世紀末偉大的自然主義作家們絞盡了腦汁。然而對霍姆斯而言,社會就是波士頓,他是在這個城市裏的桂冠詩人。私人之間的笑話,講究飲食和談吐,一點自滿,甚至還有一點與生俱來的(當然也是有教養的)謔意:這些特點在牛津與康橋也並非罕見。說不定這些都是知識份子社會的副產物。無論如何,我們好像不應該過分責備雷姆斯和他的波士頓,特別是因為他喜歡那個地方,我們常聽人們說,美國作家過於喜歡模仿惠特曼,不去親近一個比較小的地方而去親近整個美洲大陸。然而,可惜得很,不論我們怎樣為霍姆斯平反,我們也無法使他成為一個偉大作家。他的作品沒有永久性。即使他的最好的詩《副主祭的傑作;或奇妙的"單馬車"》('The Deacon's Masterpiece; or, The Wonderful "One-Hoss Shay"),也不過以輕鬆活潑取勝;至於他的成名之作《洞穴裏的鸚鵡螺》('The Chambered Nautilus'),和朗費羅的《生命頌》一樣,也無非是勸善規過,音韻和諧,一篇平淡之作而已。霍姆斯的那些小說都不夠精煉;它們顯示了一顆追根問底的心,在向四方探索。《早餐桌上》那一系列的書有同樣缺點,讀了幾章,我們難免感到不耐煩,納悶這些書為什麼寫得不如皮科克或《特裡斯特拉姆‧香迪》好。它們似乎和馬洛克的《新共和國》水平不相上下,可是你又得不到猜想書中人物代表什麼人的樂趣。在《早餐桌上》那一系列的書裏,書中人物是霍姆斯本人和與他爭論的朋友,他百無一失會把他們打倒在地,就像問答遊戲中的專家一樣。
朗費羅、洛威爾、霍姆斯三個,都不失為他們那個時代的偉人,後來卻大為退色了。他們的作品沒有份量。要找有份量的作品,我們得轉向普雷斯科特、莫持利與帕支曼等紳土派的歷史學家。他們家道富裕,無須勤苦工作,可是他們好像抵抗不住新英格蘭迫人勤勞的氣氛。(據說波士頓有一位女主人接待過一個英國來客,訪者說美國沒有有閒階級,那個女主人回答,"有是有的,只是我們把他們叫做流浪漢罷了。")新英格蘭的氣氛,也可能還把他們引向研究歷史。莫特利本來很想寫小說,試了兩次不成功,改寫文學批評也不怎樣出色,他才斷定歷史(它需要的是"工兵和礦工")比寫小說(那是"槍騎兵"的工作)更適合他的才能。帕克曼也嘗試過小說寫作(《家臣莫頓》1856年),那種硬 邦邦的自傳效果,顯然證明他不是寫小說的材料。不管新英格蘭缺少什麼,結果使文藝創作窒息,我們幾乎可以說這缺少的東西正好鼓勵了學者和批評家。就整個美國文學說,幾乎最動人的東西都不能說是"創作性的"文字。而遊記、政論、傳記、回憶錄、歷史等在美國卻都有過傑出的作品。
上述三位歷史學家都生逢其時。新大陸正需要史家。斯帕克斯和班克羅夫特等歷史學者,歌頌的是美國民主的發展。可是作為紳士派文人,普雷斯科特、莫特利和帕克曼三個人卻並不想寫美國的政治史,那樣做會使他們看起來很像為政黨僱用的文人。在他們四處尋找題材的時候,前兩位傾向於西班牙史,這一方面的研究已由歐文和蒂克納的幫助引起了普遍的興趣。蒂克納曾指導過普雷斯科特早期的研究,歐文還把科爾特斯征服墨西哥這個題材轉讓給他;普雷斯科特自己雖已著手研究菲利普二世時代的歷史,也幫助過莫特利搜集材料寫《荷蘭共和國的興起》,等於讓人把"我的題目中的精華"撇了去。帕克曼另有選擇。他在大學讀書時,就特別喜愛戶外生活,他打定主意要寫法國人在加拿大的早期活動。後來隨著興趣的發展,他說:我把計劃擴大到包括法國和英國在美洲發生衝突的整個歷程,換句話說,我要寫美洲森林史,因為這就是我對於英法衝突的看法。我的題材把我迷住了,日夜都有荒野的景象縈繞腦際。
三位史家就這樣選擇了自己的題材,不倦地工作起來。在三個人的心目中,歷史是文學的一個部門。真正吸引他們的,是題材中的戲劇成分──西班牙在十六世紀的向外擴張,民主主義和暴君政治在荷蘭的衝突,"美洲森林史"等。事實上他們三人都用戲劇來描寫他們的目標。雖然他們力求翔實並勤於搜集資料,在佈局的安排上,還是以講故事為主,希望讀起來像司各特的小說那樣有趣。其中有幾章寫的是社會史,但只要有可能,他們就要把他們的敘述和某些顯赫人物如科爾特斯、沈默的威廉、龐提亞克聯繫起來。普雷斯科特在他最好的著作《征服墨西哥史》序文裏,討論到他把戲劇性從墨西哥的陷落延長到科爾特斯的死亡,是否犯了"過早收場"的毛病;他相信他保持了"興趣的統一"。
三個人使學識和戲劇性趣味發生聯繫,在這一方面他們是成功的。當然,我們可以提出某些保留意見。作為新教教徒,三個人對於處理天主教會方面,態度上容易不大溫和──帕克曼比較好點。普雷斯科特雖然在日記裏寫"討厭的諧音",可是他寫文章的風格還是有點油腔滑調,胸部氣得腫脹,對於人物有時大量採取對比手法,如把"文雅的國家"拿來和"野蠻的國家"對比。講到莫特利,他把他的壞人寫得過於無賴,把他的英雄寫得過於英勇,看了使人厭倦。他和普雷斯科特(他比較好些)在處理資料來源時有時有點潦草。帕克曼間或在文章裏流露了高傲的態度。不過這些缺點,比起他們筆下動人的故事和他們敘述的技術來,就微不足道了。
帕克曼是三人之中最了不起的。他最初引起人們的注意的是《草原千里》,這本書現在仍以這個名字而知名,裏面寫的是他剛從哈佛畢業,和平原上的印第安人住在一起的經歷,他在一八四六年去訪問他們的時候,那些印第安人還很強大,雖然他們已經與白種獵人和移民篷車有了接觸。他還不知不覺地洩露了自己的性格。他顯示他自己是個充滿自信、不怕吃苦(幾乎是自討吃苦)的人,有一點瞧不起印第安人,更瞧不起他在途中遇到的那些趕著運貨馬車走向西部的粗野白人。那些高貴的野人在他看來至少有一半是神秘的,但並沒有因為神秘而失去我們對他們的興趣。我們可以稱之為君子的品質引起了帕克曼的欽佩;他寧願荒野上住著有教養的人。可是這些人必須堅強:他最喜歡用的一個詞就是大丈夫氣概。
在帕克曼的主要歷史著作中,也可以看到他的這些偏愛,雖然不太明顯。他的這類著作,如按年代排列,應從《法國在新世界的拓荒者》(Pioneers of France in the New World)到《蒙卡目與沃爾夫》(Montcalm and Wolfe)。《龐提亞克謀反始末》並非正式屬於這一系列的巨著。他尊重真實並不下於大丈夫氣概,放心他批評朗費羅把阿卡迪亞人(在《伊凡吉林》裏)和印第安人(在《海華沙之歌》裏)寫得過於多愁善感,他譏誚庫珀故事的佈局過於牽強。他在自己的著作裏竭力避免這些缺點。一方面他熟悉自己的寫作背景──他認為這是史家必須寫本國歷史的一個原因── 一方面他又到公文檔案中去尋根問據,因之他的敘述是建立在穩固的事實基礎上的。晚近學者發現他偶然有錯,或者不無歪曲,儘管如此,帕克曼仍然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歷史學家。他對於歷史的解釋不像莫特利那樣牽強。作為一個新教教徒,他相信英國殖民地遠較天主教加拿大殖民地開明,因之也是遠為成功的社會。但由於他對拉薩爾、法朗提那克、蒙卡目等主要人物的勇氣極為傾慕,便將上面那種信念抵銷了。實際上使他陶醉的,正是這些人在事業上的哀怨,而這些東西也使他的著作有了感染力。他的著作中有一種隱藏的自傳成分,說不定所有生動的歷史著作也都是這樣的。帕克曼筆下的人物都很寂寞,他們在荒原上奠定了他們的事業,而廣闊無際的天地既使他們的成就顯得渺小,也顯得崇高。像拉薩那樣的人物並不受人歡迎,他們的部下就不服從他們的領導。他們的結局往往是受辱,被人出賣,或是死亡。美洲對塑造美洲歷史的貴族一概加以揚棄,這是帕克曼的《法國英國與北美洲》的一個隱蔽的主題,可是他對這個主題出以冷靜的態度,處理得極其謹慎。他的文章滔滔不絕,穩健有力,緊密細緻。在我們斥責紳士派文人華麗纖弱以前,必須對帕克曼情感的改變加以考慮,他曾把他夢想中的荒野和科立奧雷那式的英雄末路感寫成了一系列記述性的輝煌巨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