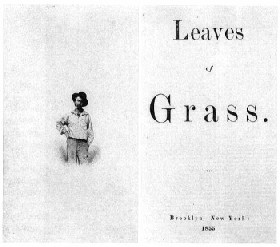
赫爾曼‧梅爾維爾 (Herman Melville, 1819-91)
生於紐約。父親經營進口生意,起初業務興隆,後破產,卒於一八三二年,遺下妻子兒女(後移居紐約州奧爾巴尼)。在親戚的援助下,勉強維生。梅爾維爾曾在銀行工作,也教過書。一八四一年搭捕鯨船阿庫什尼特號去南太平洋以前。曾以船上侍者身份去過一次利物浦。一八四二年他在馬克薩斯島棄船潛逃,碰到吃人的野人,後來搭澳洲捕鯨船離開群島。其後他又到塔希提島和檀香山闖過一陣子江湖,於一八四四年乘美國號快速帶帆戰艦返美。開始根據航海經歷從事寫作:《泰皮》(Typee,
1846),《歐穆》(Omoo, 1847,他於是年結婚),兩書均受歡迎;《瑪地》(Mardi, 1849)、《雷得本》(Redburn,
1849),《白外衣》(White-Jacket, 1850>,《白鯨》(Moby Dick, 1851),《皮埃爾》(Pierre,
1852)。其中《瑪地》使人感到迷惑,《白鯨》不受歡迎,《皮埃爾》徹底失敗。其後逐漸放棄寫作生涯,但也完成若干短篇,其中六篇收集在《廣場故事》裏(Piazza
Tales, 1856),和另外兩部小說,《伊斯雷爾‧波特》(Israel Potter, 1855)和《騙子的化裝表演》(The
Confidence-Man, 1857)。他隨後轉而寫詩,其中大部分包括長詩《克拉瑞爾》 (Clarel, 1876)在內,係由私人出版。一八六六至一八八五年在紐約任海關檢查員;終於退休,靜度餘年,臨終前數月寫成《畢利‧伯德》(Billy
Budd),直到一九二四年才出版。
華爾特‧惠持曼(Walt Whitman, 1819-92)
生於紐約長島,是荷蘭人和美國北方人的混合血統,父親是木匠。一八二三年,從曼哈頓越過東河遷居日趨繁榮的布魯克林鎮。一八三○年輟學去做印刷學徒;一八三八年到三九年在長島教書,一八四-年到四五年做新聞記者:一八四六年到四七年任《布魯克林鷹報》編輯在政見上與民主黨發生爭執;被人認為是一個懶惰的編輯,結果去職。一八四八年小遊新奧爾良。一八五一年到五四年在布魯克林當木匠,用筆記本隨手記錄詩篇,這些詩十一八五五年結集出版,題名《草葉集》(Leaves
of Grass)。這些詩篇受到愛默生和另外幾個人的讚揚,也受到一些評論家的詆毀,但一般來說,不大受人注意《草葉集》一八五六年再版;一八六○年三版。一八六三到六五年在華盛頓任公務員及醫院看護,照顧內戰傷兵。一八六五年出版《桴鼓集》(Drum
Taps)。《草葉集》在一八六七年、一八七一年、一八七二年、一八七六年、一八八一年、一八八九年、一八九二年連續再版。惠特曼繼續在華府供職,直到一八七三年中風,半身癱瘓,終生未癒。一八七一年出版散文《民主遠景》(Democratic
Vistas)。一八七九年到美國西部和中西部旅行。一八八二年出版自傳式筆記《典型的日子》(Specimen Days and Collect)。晚年有弟子環侍左右,在文人之間甚為知名,但仍未為一般人所知。一八八八年出版詩歌散文集《十一月的枝椏》(November
Boughs)。死於新澤西州的坎登。終身未娶。
愛默生和霍桑雖然都到過歐洲,但他們像梭羅一樣,都只從身邊找拾文學上的寫作素材。新英格蘭縱然不免孤陋,畢竟養育了他們,一如其他新英格蘭人,他們確實也從本鄉本土攝取了某種靈氣。可是梅爾維爾多年在海上漂泊,這就使他遠離了紐約和奧爾巴尼那個熟悉的世界。把海洋當做獵取比喻的豐富源泉,當時不只梅爾維爾一人。和他同時代的福樓拜爾(Flaubert)就曾在一八四六年說道,"人世間有三大傑作:海洋,《哈姆雷特》和莫札特的歌劇《吉歐梵尼先生》"。要是霍桑當年接受邀請,前往南太平洋作一次航海旅行,在寫作上說不定會對他大有裨益。無論如何,梅爾維爾和上述諸人不同。他真的航過海,因此他能夠用親身經歷支援他離奇的想像。如果說海洋是種象徵,同時它也是一條謀生之道。實在說,在梅爾維爾早期幾部作品裏,他注意的是寫實,但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寫實。《泰皮》給讀者描寫了一個新鮮而富有刺激性的場面,用自傳方式敘述,使看厭了旅遊隨筆和海上奇談的讀者,觀感一新。事實上,雖然有一部分材料是梅爾維爾想像的產品,但他似乎並沒有把這本書當做小說看待。他在序文裏說,他"急著要把絲毫未加渲染的實際情況敘述出來"。他在那部小說裏插印了一幅地圖,還加了一些文件式的篇章。(在英國出版時,書名叫做《馬克薩斯群島山谷與土人同住四月見聞錄》(Narratives of a Valley of the Marquesas Islands),或《波利尼西亞人生活一瞥》(A Peep at Polynesian Life),就憑這個書名,保證不能把它列入小說一類。)它的文體,大體上說,正是一位旅人在抒發其妙筆文思:
初次來到南太平洋的人,在海上見到那些島嶼,對於它的外貌,一般都會感到驚訝。從那些描寫群島美麗景色的模糊記載裏,許多人往往只是想起一幅加了油彩的畫:徐徐高起的平原,有清幽的林蔭覆地,有溪流縈帶……
《泰皮》是一篇用第一人稱自述的記載,寫的是一個美國青年的冒險。他和同伴托比私自離船出走。二人爬過一座大山,進入山谷,碰到一些吃人的泰皮人。托比逃脫了,他本人被迫與土人同住。使他吃驚和安慰的是,土人待他很好。這個故事的結尾,寫他從野人處逃走,野人一路追他追到海裏,一條大船上放下小艇把他救了起來。這個簡單故事的要點,在於文明社會的邪惡與野蠻人的美德之間的對照。那些野蠻人,具有內在美,全都無憂無慮。那個美國青年還和其中一個發生了純樸的但非十分生動的愛情。《泰皮》在創作上固然沒有什麼重要,不過梅爾維爾在後期比較成功的作品中所表現的主題,幾乎具體而微地都可以在這篇東西裏找到。在這部書裏,他敘述的是旅途和航程中的經歷;他譴責白人文明(沒有什麼獨創的見解,引用了盧梭的話)和它那一堆道德法規。他暗示那個流浪的年輕人,不論在自己人中間,還是在野蠻人中間,都不可能得到滿足。托比雖然是個快樂而外向的人,梅爾維爾依然說他是一個"你在海上有時遇到的漂泊者,從不吐露他的出身,從不提到他的家,似乎受了什麼無可逃避的神秘命運的驅使,在世界上到處流浪。"寥寥幾筆,勾畫了他在《白鯨》中又提到的那種人物巴金頓,驚鴻一瞥,但使人難忘。
《泰皮》以主人公逃亡結束,在《歐穆》裏,故事從這裏開始。在這裏,梅爾維爾安排了一個更加不祥的環境,那個年輕的美國人現在置身於一條舊得不能再用的捕鯨船上,船員心存叛亂,船長軟弱無能。死了一個人以後,有水手預言,三個星期以後,活在船上的,不會多過四分之一了。這條船顯然在劫難逃了。可是緊張局勢終於緩和下來,叛變演變成滑稽歌劇的場面,唯一嚴肅的地方是把塔希提島奚落了一番。這個島上的居民身體受到白人疾病的戕害,文化受到善意的傳教士的摧殘,只有等待絕種的份兒。他們唱著舊日的預言:
棕擱要成長,
珊瑚要伸張,
可是人啊,卻要死亡。
輕鬆愉快的場面又插了進來。敘述故事的人,在他的奇形怪狀的老友長鬼博士陪伴下,在島上到處漂流,直到他打定主意坐美國捕鯨船離開塔希提,故事也就這樣一走了之了。
《歐穆》進一步使讀者認識到梅爾維爾是個長於描寫愉快而生動的回憶的作家。但是緊跟著出版的《瑪地》,卻是另一回事。《瑪地》開始時平鋪直敘,雖然文字比較華麗:
我們出發了!下桁大橫帆和中桅帆均已揚起;掛有珊瑚的錨在船頭吊著晃來晃去;三支最高的桅帆給輕風吹動,輕風像獵犬的吠聲一路跟著我們。船桅上下的帆均已張開,帆槓向兩邊伸出,加上許多副帆,使我們看起來像只張開兩翼的鷹隼,將帆影撒在海面上,搖搖擺擺地劈開海水。
在這短短一段文章裏,他用了兩個直喻和一個新創的副詞,在這裏可以看到後期的梅爾維爾的影子。不過《瑪地》的筆調是活潑的。雖然敘述故事的人抱怨這次出海捕鯨,旅程單調乏味,可是在書中他仍然是個精力充沛、無拘無束的青年。他的教育程度高於同夥,可是同他們並不見外。不久以後,故事敘述人塔紀──在大半部書裏他都叫這個名字──決定逃跑,用捕鯨船上一隻小艇來行事,帶了一個老水手和他同行。他們向西駛向太平洋中一列島嶼;他們的冒險事跡真夠刺激,可是完全合情合理。
跟著形勢變了。塔紀在海平線上看到陸地的時候,也看到一條當地土人使用的小船,船上有幾個年輕的武士,後來才知道他們都是老祭司的兒子。老祭司坐在船上看守著一個名叫伊拉的可愛的白種女郎,女郎就要給他們拿來祭神了。塔紀為了拯救這個女郎,殺死了老祭司。在這裏梅爾維爾突然把故事改變了,把文章寫成熱鬧的通俗鬧劇了。
可是他又轉了筆鋒。塔紀一行到達瑪地群島以後,土人對他敬如神靈。在伊拉失蹤以前,他們一直過著神仙般的日子。他打定主意要踏遍群島尋找伊拉,於是帶著四個瑪地人(其中有哲人白巴蘭札),踏上征途。大半部書記述的就是以塔紀為中心的旅程,伊拉只不過是他們旅行的藉口,故事重點只在他們所看到的事物上面。當然,有時也提到伊拉,也敘述老祭司的三個兒子如何一直在追蹤他們,還把兩個作者認為多餘的人物幹掉了。但所有這些,都被洪流般的諷刺和關於瑪地世界的思索淹沒了。諷刺深度不同,層次也不一樣。有些海島代表人類的愚昧(宗教上的教條主義,對於出身的驕傲),別的島嶼象徵實實在在的國家(多敏諾拉指英國,韋文札指美國)。沈思默想也同樣在嚴肅與滑稽之間上下波動。塔紀在敘述時與作者合而為一,但是他們會被長時間擺在一邊,反而讓白巴蘭札和其餘的人去爭論生存的意義。偶然悔爾維爾一塔紀私下也沈思默想,或寫些古怪的抒情式的幻想:
夢!夢!金黃色的夢,金黃而無止境,像野花遍地的草原,從裏約薩克拉門托向外延伸……;草原好似沒有稜角的永恆:踏扁了的黃水仙葉;我的夢多得像水牛,吃草一直吃到天邊,吃遍世界,我用長矛向其中一隻刺去,想在它們逃散以前,刺得一個。
他寫東西,就像他在同一章裏說的,好像一個有神靈附體的人,一心一意去尋找──像他讓白巴蘭札所說的:
事物的精髓:未知世界裏的奧秘;笑聲引發的眼淚中的內因,表相下面的真實;粗糙的牡礪殼裏的珍珠。
書要收尾的時候,那幾個航海者找到了寧靜島,那裏充滿了真摯的愛與和平。他們請求塔紀放棄對伊拉徒勞的追尋;可是當他發現她已淹死在老祭司給她安排的漩渦裏,就獨自駕船離開平靜的礁湖,駛往洶湧的大海;祭司的兒子們還在追他。開始時的海上船歌,如今成了痛苦的呼聲了。從馬裡亞特或是庫珀的理性世界,我們進入了很容易讓人想到的愛倫‧坡《阿瑟‧戈登‧皮姆的故事》的世界(這個故事開始時也很合情合理,但以怪異的災難結局)。霍桑描寫這樣的場面,會在災難之前懸崖勒馬,對是梅爾維爾和愛倫‧坡一樣,總有一點欲罷不能。就梅爾維爾而言,是他旺盛的元氣,在愛倫‧坡,是他的才智,引起了歇斯底里。《瑪地》是一部寫得歇斯底里過度緊張的書,在創作意圖上混亂到無可救藥。可是它們不失為一部挺好的壞書。在讀精彩的《白鯨》以前,把這本書研究一下,是非常有趣味的。
梅爾維爾寫了《瑪地》以後,繼續寫作,幾乎沒有間斷。可是在這個階段,也許他已經覺察到他把自己和讀者搞得過於吃力,便多少回到了《泰皮》和《歐穆》的格調。在《白外衣》裏,他寫的據說是他在美國戰船"美國號"上的經歷。《雷得本》詳細敘述了他初次來回航行於紐約與利物浦之間的經過。在這本書裏他又以直率的敘述者的身份出現,好像不敢信任自己有虛構的能力似的。文筆也簡練了,雖然比起《泰皮》來要柔和。下面是他在《雷得本》裏用兒童的眼光對於一幅油畫的描寫:
上面畫著一條看來很臃腫的噴著煙的船,船上有三個戴著紅帽的大鬍子,捲起褲腳,正把拖網拖上船來。一角畫著一塊像是法國風光的高地,上面有一座破爛的灰色燈塔。波浪是烤得焦黃了的,整幅圖畫看起來古老而圓熟,我常想吃它一塊,味道可能不錯。
除去"大鬍子"這個詞以外,這段寫得很好的描述,和《瑪地》那種華麗浮誇的文字,毫無相似之處。
如上所述,他在短短幾年內,寫了五部書,可是都不大好列為小說。前三部寫的是南太平洋;船上發生的事情雖然不少,是真正使梅爾維爾著迷的,主要還是那些島嶼,或者不如說是那個地區的整個熱帶風光。另外兩部,《白外衣》和《雷得本》,寫的不是熱帶,在《雷得本》裏雖然有一段很長的陸上插曲,兩部作品對於把船員當做人類縮影,把航程(而非著陸)比喻為人類的命運,表現了極大的興趣。梅爾維爾在開始寫作的那幾年,讀書既廣且深,他的作品裏有狄更斯的痕跡,也許在他較晚的《錄事巴托比》('Bartleby the Scrivener')之類的作品裏最為顯著,其中所描寫的法律和律師世界裏那種沈悶的非人性格,似乎反映的是《荒涼山莊》的情調。人們也不知道梅爾維爾有沒有讀過英國人內德‧沃德所著於一七六O年最初出版的一本輕快而胡調的小書。這本書名叫《從一條戰船看麻木的世界》。它對船長的描寫是這樣開始的:
他是個巨無霸,或者海神,可憐的水手們崇拜他就像印度人供拜魔鬼一樣。由於恐懼而非出於敬愛,甚至有人說他比魔鬼更可怕。
拋開這些可能的根源,顯而易見,托馬斯‧布朗等雖然使梅爾維爾發生興趣,莎士比亞給他好處卻最多。
此外,在他寫完第六部著作初稿的時候,他特別鑽研了有關捕鯨的事,和它結了不解之緣。在上一部著作裏,有許多地方看出他對於傳統性的記載並不滿意,他希望他的冒險故事有更大的意義。在閱讀和結識霍桑以前,沒有人鼓勵他去注意他所謂的"本體論的中心人物"。可是他在霍桑身上找到了另一個美國作家,關心"表面以下的內涵",並以小說為表達形式。使梅爾維爾遺憾的是,後來二人的交情日疏。可是在他寫《白鯨》時,這段友情對於他卻是十分重要的。說不定促使他把這本書改寫,獲得更深一層的意義,也是由於這段友情。
在《白鯨》中,他選擇了一次乘捕鯨船到南太平洋的航行為背景。這次他把焦點始終放在船上,而不是遨遊於真的或假想的島嶼之間,這樣,他就給自己找到了一個堅實的社會與職業構架。有了現實的根據,他可以任由他的想像馳騁。哲學上的玄想出自實際情況(不像霍桑那樣把本末顛倒)。《白鯨》的初稿,很可能在處理上過於偏重記錄──有些章節,現在還是這樣──模仿的是歐文‧蔡斯的著作。在定稿裏,把捕鯨的事集中在一條鯨身上──白鯨莫比‧狄克和船長埃哈伯對於莫比‧狄克的著了迷似的仇恨上面。小說具有極大的力量。它氣勢磅礡地周旋於刺激與平靜之間,在追逐白鯨的三天裏,場面達到了幾乎難以忍受的緊張程度,最後出現不可避免的災難──白鯨殺死了埃哈伯,然後像歐文‧蔡斯的艾塞文斯被撞毀那樣,"佩闊德"號捕鯨船也被白鯨撞毀了。關於動作的描寫沒人可以超過他,梅爾維爾的功力彷彿在這裏找到了適當的表現。他筆下的航程、水手、捕鯨船、船長、那條鯨,都寫得栩栩如生:它們都有份量、幅度和色彩。此外再加上豐富的內蘊,這可不像《瑪地》裏古怪的說教和牽強的探索人生的意義。比如說,伊希梅爾、伊萊賈、加布裏埃爾、埃哈伯等小說中人物,都起了聖經上的名字,可是一點都不牽強,這在書中所講的新英格蘭,是自然不過的事情(就像古德曼‧布朗的妻子名叫"信仰"一樣自然),這樣一來,梅爾維爾就可叫順理成章地到聖經中去找類似的人物了。
埃哈伯倒有幾分像霍桑筆下的典型人物。我們在霍桑的《大紅玉》('The Great Carbuncle') 裏,看到一個年老的尋寶者,他在山中徘徊,尋找那件寶貴的東西,可是沒有希望。
從中得到快樂,那種癡心妄想早巳消逝了。我一直在尋找那塊倒楣的石頭,因為我青春時代的狂想野心,已成了我暮年不能擺脫的命運。追逐是我力量的來源,元氣的寄託,和血液裏的熱,骨頭裏的精髓!……我就是放棄了尋找大紅玉的希望,虛度的年華仍然一去不返了! 找到它以後,我將把它帶到某一個巖洞裏,在那裏,我將緊緊抱住它,躺下死去,要它和我永遠埋葬在一起。
這是一個離群索居的人,被魔鬼迷住的夢想者,像海德格醫生和伊桑‧布蘭德那樣,命裏注定要過妄自尊大的孤獨生活。由於霍桑描寫這些人物是誤入歧途,他們的邪惡往往難以置信,而且你對大紅玉之類的目標,也不能過於認真。然而我們用不了多久就被埃哈伯的性格和他的問題迷住了,他這個'莊嚴的、不敬神的、神一般的人","雖然受了創傷",還"有他的人性",而且他的目標是可以讓人相信的。埃哈伯像梅普爾神父在他動人的講道裏所講的約拿一樣,是故意造孽,因為"如果服從上帝,我們就必須違抗自己"。可是在同一篇講道裏告訴我們,勇氣和驕傲,都是美德:"願那些反對現世界的驕傲偶像和船長及永遠堅持不動搖本性的人們得到喜悅。"霍桑覺得一切過分的舉動都是可悲的;梅爾維爾對於人類的潛力有比較寬容的認識,認為無論善惡都是由於把事情做過頭一些。這麼一來,埃哈伯既是英雄,也是惡人,塔紀決定的只是自己的命運,而埃哈伯卻決定了許多別人的命運。
《白鯨》是世界上一部偉大的小說,越讀越覺得它有味道。它的一些小毛病,使我們想到梅爾維爾多產時代的作品。在《瑪地》裏,雖然塔紀被認為是講故事的人,可是我們不知道到底是誰在講故事。在《白鯨》裏,混亂也很明顯。小說開頭第一句話,"我名叫伊希梅爾",響亮地預先通知我們誰是敘述人。然而伊希梅爾採取的是鬧著玩兒的態度,吊兒郎當而非鍥而不捨,他好像與梅爾維爾過去作品中作者兼敘述人的人物沒有兩樣。"上帝什麼事都不讓我做完,"他在第三十二章中這樣喊道。"這一整本書只是一杯酒──不,只是杯中的一口。啊,時間,力量,金錢,忍耐。"這當然是作者的旁白。土人魚叉手奎奎格對他很好,伊希梅爾確曾透露過和他的名字比較符合的複雜性,他說、"我的破碎的心和發狂的手不再抗拒達豺狼似的世界";可是以後在小說中並沒有任何情節證明這個青年是那樣一種人。一般來說,他很像《泰皮》中的敘述人,他所以和奎奎格相好,也為了要強調原始的道德價值。然而他把這個主題拋棄了。梅爾維爾似乎發現伊希梅爾是個討厭的人。前二十八章由他敘述故事。跟著的三章(由"埃哈伯登場,斯塔布跟來"開始)故事顯然並未由他敘述,因為他不可能知道別人的獨白。後來雖然又重新讓他敘述,但常被棄而不用。我們可以說梅爾維爾猶豫不決到底由誰來負責這部小說,他也不能決定它該是一本什麼性質的書。他之竭力模仿莎士比亞武的獨白,我們可以認為,他是想借此來給小說開拓一些寬度(只是手法有欠高明),把它從伊希梅爾的狹小天地中挽救出來。故事一路發展下去,的確《白鯨》很快有了改進;我們可以說塔紀已經分成兩個部分,即伊希梅爾和埃哈伯,不過伊希梅爾和梅爾維爾仍在掄著敘述故事罷了。
我們必須重覆一遍,這些只是無關緊要的缺點。話雖如此,把這些缺點拿來和梅爾維爾的下一部作品《皮埃爾或者是暖昧》對照觀察則仍有其重要性。梅爾維爾寫完《白鯨》不久就寫《皮埃爾》,他在完成《白鯨》時,心裏一定有了《皮埃爾》。和《瑪地》一樣,《皮埃爾》失敗得非常慘,可是出奇地讓人難以忘記。在這部小說裏,梅爾維爾初次離開海洋和遙遠的地方,而用第三人稱來寫當代的美國。皮埃爾是一個得天獨厚的青年,命運給了他一付漂亮的儀表、良好的家世、才能,甚至一個美麗的未婚妻。後來另外一位女郎進入他的生活。她說她是他所敬愛的亡父的私生女。他非常喜歡這個女郎,知道母親永遠不會承認她,也不會容忍丈夫的過失。經過一陣子哈姆雷特式內心煎熬──那時皮埃爾讀的書裏面就有哈姆雷特──在近乎愚蠢的寬宏大度驅使之下,他把他的異母妹妹借到紐約,讓人相信,他由於突如其來的迷戀而娶了她。他這種行為的確驚人,母親活活被他氣死,未婚妻也讓他打擊得一蹶不振。他一文不名,把異母妹安置在破蔽的寓所裏,開始以寫作為生。但是他是在絕望中寫作的,寫出來的是一本瘋狂的書,哪個出版商都不肯碰它。故事以流血慘劇結束,所有主角全都死亡。《皮埃爾》大部是趕時髦的鬧劇,中間夾雜一些對了當時文壇和社會改革分子滑稽可笑的諷刺。像愛倫‧坡筆下的許多主角一樣,皮埃爾其實是作者的一個投影,他也同樣透露了作者和美國疏遠的程度。過去梅爾維爾是個狂熱的民主主義者,譬如說他也像惠特曼那樣,反對他所謂的莎士比亞對於貴族階級的奉承。然而漸漸的他的民主信念有了限度,公眾的愚妄(一部分表現在對於他自己作品的態度),和人類邪惡的表露,使他的樂觀情緒受到打擊。他把皮埃爾寫成一八○○年型的貴族,生活在一八五○年時的美國,只有痛苦和無依無靠。以前他還可以設法辨別人民與公眾的不同,現在只能用一個名叫"普洛蒂努斯‧普林利蒙"的人寫的小冊子來安慰皮埃爾了。這本小冊子說普通人可以達到的最高的目標,只是一種善良的權宜之計,即使是最為傑出的人,他能達成的善,也不會比這個更加嚴密:整個看法都被一種超然的態度緩和下來了。這本小冊子對於皮埃爾也沒有產生任何好的影響,因為他信手一放,不知道把它放到了什麼地方,反正他也不會比塔紀和埃哈伯更有理性。然而這正足以證明梅爾維爾的垮臺,因為三年以前他還能在《雷得本》中說
高於這個世界的世界,哥倫布時代以前虔誠的人所馨香祈求的,在新世界裏找到了;首次碰到這些地方的深海探測錘,把地上樂園的土壤帶了上來。
梅爾維爾在《皮埃爾》問世以後,慢慢放棄了寫作生涯。他繼續寫了幾年散文,包括一部異常枯燥的歷史小說《伊斯雷爾‧波特》,敘述故事的美國人,無原無故在倫敦過了四十年流亡生活;還有《騙子的化裝表演》,在這部小說裏,梅爾維爾坐了密西西比河上比較平凡的輪船出去航行。約莫在這個時候,梅爾維爾的朋友霍桑說他,"他既不能相信,又不能任令自己不信,因為他為人誠懇,敢作敢為,他在二者之間必須有所選擇。"《騙子的化裝表演》顯示的就是這種百分之百的困惑。故事中的每一樣東西可能是另外一樣東西,一種假託,一種前後矛盾的事物。在這個例子裏,梅爾維爾所寫的航行,是在萬愚節那天進行的,乘坐的是挖苦地命名為"誠實號"的輪船。船上有一連串壞蛋或是騙子──看上去是以各種形相出現的同一個人。美國人動不動就想騙人還是被騙,是一個大有可為的題材,跟著我們就會在馬克.吐溫的《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裏看到那一對旅遊中的無賴。但是梅爾維爾並不以逗樂為滿足,不管它有多可笑。因為他對真實與幻影念念不忘,他讓讀者看了他的故事,像"誠實號"船上那些旅客那樣莫名其妙。有信心是聰明還是愚笨? 我們對待信任,應該全部相信,還是全不相信? 如果說自己騙自己是快樂的一個先決條件,難道騙子不是一個非常必需、甚至萬萬少不得的人嗎? 酒醉之後是使現實模糊不清,還是更加接近現實了呢? 這部小說的用意,一如《伊斯雷爾‧波特》和梅爾維爾在一八五O年代寫的幾個短篇,好像都是"普洛蒂努斯‧普林利蒙"小冊子的變種。南方各州醞釀脫離聯邦;繼梭羅宣佈脫離社會,廢除奴隸主義者加裡遜當眾焚燬美國憲法以後,梅爾維爾在這裏暗示,我們說不定可以看客的身份逃過這場劫難。脫離並非永遠可能,誰都不能像梭羅脫離得那樣乾淨利落:"班尼托‧西蘭諾"陷在邪惡的網裏, 完全為心術不正的黑奴巴博所控制,他只能"跟隨他的領袖"照樣死亡。或者,就是逃脫了,我們也會像《錄事巴托比》那樣死去。這並不是說梅爾維爾已經江郎才盡,或者他在這個時期寫的短篇都是失望消極的。事實上有一篇《蘋果樹桌》,就用了一個有希望的象徵,"強壯而美麗的甲蟲",木料雖已製成傢俱,它還是從裏面鑽了出來,梭羅的《華爾騰》,也是以美麗的甲蟲結束的。有些短篇雖然很好,然而它們所表現的是梅爾維爾已經不再願意和他的環境奮鬥了。
一八六一年內戰爆發的前幾年,梅爾維爾由散文轉向詩歌。等到他死的時候,寫成的詩足以印成一大厚冊。長詩《克拉瑞爾》尚不包括在內。這首長詩寫的是參加聖地來去的情形,既寫實又有象徵性。我們可以把愛默生批評梭羅的話拿來用在梅爾維爾的詩人他的天分要比他的才能好得多。梅詩在技巧上是拙劣的,或者只有十幾首詩和《克拉瑞爾》的某些片段,讀了讓人覺得十分滿意,就是這少數詩在音韻上也不是完全無懈可擊的。其中寫得最好的是有關內戰的幾首。在梅爾維爾的眼裏,一如在惠特曼的眼裏,內戰是一件十分悲慘的事,就某一點而言,證明他沒有看錯:
自然的黑暗面現正倡狂
(啊!樂觀者的歡呼在失望中逡巡逃避)
不過他對美國留下來的信心,始終沒有完全消滅,使他悲哀地揣測,即使得到勝利,也會像人的最後墮落:
開國元老的夢想將會逃逸無蹤。
將來世世代代如此
正如過去世世代代一樣。
不過這場衝突使他恢復了他的人類尊嚴感。戰爭結束以後,在七十和八十年代,梅爾維爾的詩主要是勸人接受現實。有時,比如在《大冰塊》('The Berg') 和《馬爾代夫之鯊》('The Maldive Shark')中,有了沈重的憂鬱,有時它又提升到幽怨的輓歌或的情調:
何處是我們漂泊過的世界,內德‧布恩?
梅爾維爾最後一部作品是《畢利‧伯德》(Billy Budd),一篇相當長的短篇小說,似乎是梅爾維爾一生中的一個尾聲。在這篇小說裏,他又回來敘述船上生活,和船上從上到下嚴格的紀律與生活中詩一般的情趣。同時他又回到他在早年愛好的一個構想,一個伊阿戈型的壞蛋(如《白外衣》中的布蘭德和《雷得本》中的傑克遜),這種人的動機純粹是邪惡的,因之他不像一般小說中的反派人物,他固然應該受人憎恨,但更應該受人憐憫。糾察長克拉加特誣告純潔青年畢利‧伯德鼓動叛變,被畢利打死;畢利必須償命。克拉加特是邪惡的,不過他對於畢利的憎恨,是一種用細微的筆觸處理的感情衝突。不過人們把畢利的基督般的本性和維爾船長慈父般的性情,說得未免過火,為了要証明這一點(根據一個解釋),梅爾維爾終於在基督教義裏找到了安息的地方。無論如何,畢利被認為是無辜的,維爾是公正的。然而要畢利來負擔晚近批評家對於他所作的諸般解說,他就顯得過於單純了;也許梅爾維爾好高鶩遠的日子已成過去,這時寧願用一個歷史寓言來說明無辜的牽累,寓言講的是在過多的平等之後,要強加一點秩序。秩序是不大公平的,不過對於疲倦的人都是一種安慰。難道畢利‧伯德沒有一種消極的、被虐待的性格? 梅爾維爾似乎在說,失敗為人人所不能免,為什麼還要像塔紀、埃哈伯、皮埃爾那樣去奮鬥呢? 我們寧可像畢利那樣,振起一種悲哀的不可瞭解的尊嚴,像《歐穆》中那些塔希提人的尊嚴,
"就只把那些腕上的鐐拷解開,
讓我好好地翻過身,
我睏了,帶著濕泥的海藻纏繞著我。"
華爾特‧惠特曼
(Walt Whit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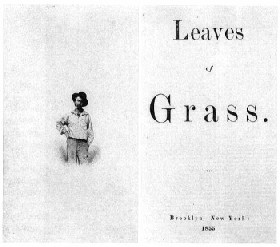
(American Memory Collection, Library of Congress)
和梅爾維爾同時代的華爾特.惠特曼,也是紐約州人。二人之間有一些相同之點:有熱情洋溢的一面,也有退縮的一面;有男性的精力,也有女性的(或者同性戀愛的)沈靜。惠特曼的《曼納哈塔》('Mannahatta')寫道:
匆匆的和閃耀的流水的城市! 塔尖與桅檣聳立的城市! 蹲在海灣裏的城市! 我的城市!
聽起來很像《白鯨》第一章裏的"海島城市曼哈托斯,周圍一帶儘是碼頭"。在同一本書裏,梅爾維爾也像惠特曼那樣歌頌民主的尊嚴,"一條揮舞十字鍬或者敲打鐵釘的臂膀"。他們兩個對於海洋都有無盡無休的興趣:惠特曼認為它是偉大的有節奏的脈搏,波濤放蕩,像他的詩的那種格調。在梅爾維爾的作品裏,也有惠特曼詩裏那種超驗論的說法:"啊自然,啊人的靈魂!" 埃哈伯喊叫,"你們之間的相像是多麼難以言傳啊! 最小的原子也不活動,也不依賴物質而生存,然而,卻與人心心相印。"
當然梅爾維爾和惠特曼(兩個人彷彿沒有見過面,對於彼此的作品也漠不關心)在別的方面是不相同的。雖然梅爾維爾像惠特曼一樣具有一種新英格蘭氣質中所缺乏的熱情和活力,但在心智方面,他和他的朋友霍桑的關係,似乎比對惠特曼更加密切;在陽光照射著的波浪下面藏有妖怪,和沈船的威脅。我們在惠持曼的作品裏就找不到這種隱藏著的災難;惠特曼在對比之下比較接近愛默生,雖然他後來不大願意承認,早年他受愛默生作品的影響非常之深。下面這兩段話都是從他們的筆記裏採摘下來的,從裏面可以看到二人的近似。先看愛默生:
二三十年來我寫的和講述的東西,有人一度認為新奇,而我現在並沒有一個弟子……我樂於把他們從我身邊趕開。如果他們纏在我身邊,我還能做什麼呢? 他們會妨礙我,打攪我。我因為沒有門生而感到自豪。假如學派不能創造獨立見解,那麼我便要說它的洞察就不怎樣純潔了。
惠特曼是這樣說的:
我不願意做一個偉大的哲學家,樹立任何學派。……不過我願意把你們之中的每一個人帶到窗前……我用左臂摟著你們的腰,用右手把無止境無源頭的路指給你們看。……我不能──上帝也不能──替你們走這條路。……
這些話當然並不盡同,可是極其相似。有過一陣子,批評家慣於讚揚霍桑和梅爾維爾能夠"辨識邪惡",以不屑的神氣指責超驗論者,特別是愛默生,說他們缺乏這種能力。我們並不反對對辨識派禮遇有加,可是難道我們同時非把非辨識派趕出後門不可? 說不定文藝批評永遠是對某些人有欠公正,對另外一些人又過分偏袒了。可是好像值得遺憾的是,最近有一本很有份量的書,為了稱讚霍桑,罵惠特曼不論"在哪一方面"都是霍桑的對頭,說他"敗壞了美國的詩歌和散文,比美國任何一方面的影響敗壞得都厲害。"事實上,惠特曼,一如所有偉大的作家,都是獨一無二的;從嚴格的意義上說,他不是任何人的對頭。然而惠特曼的作品確實極不平衡,一般而言,新英格蘭超驗論者受人攻擊的地方,也正是他受人攻擊的地方。"超驗論的意思是,我們的有學問的太太說(說的時候還把手一揮),稍稍超出人世以外。"我們可以把愛默生在一八三六年寫的這段札記,和惠特曼的解釋(見於他匿名對自己詩的批評!)加以比較,惠特曼說那些詩句彷彿永遠"沒有寫完,沒有定稿","永遠餘意未盡,暗示世外還有一點什麼"。像愛默生一樣,他被人指責過分樂觀和不拘形式。他的目標,用他自己那句出名的話來說,"主要是……自由、充分而真實地記錄一個人(生活在十九世紀下半世紀的美國的我)"。他要做一個"人的詩人",為全體美國人(為全人類)說話,因為他知道所有的人基本上都和他一樣。桑塔亞納反對他,認為這個學說過於幼稚,說惠特曼的直覺裏沒有內涵。.‧勞倫斯在許多方面都稱讚惠特曼,唯獨譴責他對於超驗論自命不凡,他居然能說(使用的字句使我們記起愛倫‧坡的"天上的合一")"我是萬物,萬物是我,所以我們都是一種存在中的一個東西,像那個'塵世蛋',它已經壞了好久了。
有的人不喜歡惠特曼的另外一些方面,這些,人們在愛默生的作品裏是找不到的:例如他的沸騰的愛國主義(這也許是家傳,他的父親給他三個長兄起的名字是喬治‧華盛頓,托馬斯‧傑斐遜和安德魯‧傑克遜,這種做法,當時並不罕見),以及他把量和質等量齊觀等等。南方詩人拉涅爾認為惠特曼的論調似乎是說,"因為草原遼闊,所以放蕩值得欽佩,因為密西西比河長,所以美國人個個都是上帝"。拉涅爾想到的大概是下面這樣的文字,這一段是從《草葉集》一八五五年版序文中摘下來的:
這裏不僅是一個國家,而是許多國家豐富的總合。這裏的行動,幕後沒有指揮,衝破一切繁文縟節,一大片一大片地浩浩蕩蕩向前進。
或者這一段,見惠特曼一八五六年《致愛默生書》:
世界上現有巨大的兩對、三對、四對圓筒印刷機二十四部,由蒸汽發動印刷,其中二十一部在美國。
這些話使我們記起塞繆爾‧巴持勒的批評,他說美洲不應該一下子就被發現了,應該一塊一塊地發現,每塊都有法國或德國那樣大;也使我們記起愛默生的感想,"我期待惠特曼歌頌國家,可是他只開了一個清單,似乎就心滿意足了。"
這些清單曾再三受到人們的揶揄和譏笑。他使用的辭彙也是一樣,愛默生說他的辭彙是《薄伽梵歌》和《紐約先驅報》奇妙的結合。他過分使用某些詞語如豐饒的、圓滿的;他鬧過大笑話(心裏想用種子的,卻用了猶太族的)。他創造一些奇怪的字尾;他借用外國文字,特別是法文。他使用骨相學的字眼。其結果往往極其好笑:
他們的相貌新鮮坦誠,他們的骨相豐饒堅決。……
在你的燦爛的蒸蒸日上的學者階層,在你的聲嘶力竭的講演家裏面,
在你的信奉聖潔的詩人和廣人無邊的學者裏面。
他以同樣值得懷疑的熱情,讚揚一幅描繪卡斯特最後一役的油畫,在同一行詩裏用了可愛的與可笑的詞藻,在以後的版本中他也不肯把它們刪掉。他經常修改他的詩篇,但並非每次都有改進。
事實上,惠特曼最壞的詩,壞得讓人難以想像。他對他的奇怪的文體,就像一個野人對於他從別人的垃圾桶裏取出來的禮帽那樣誇耀。到了晚年,他裝腔作勢,瞎吹亂誇,留了一把大鬍子,一派做過木匠的基督神氣,這正是使許多人反胃的那個惠特曼,而環繞他左右的弟子們,和他一樣古怪。但是那些不怕麻煩設法和他接近的人,便會發覺他的缺點反而襯托出他的成功。這個平凡的記者,這個發表文章說明"勞動人民的顯然命運",並為他們爭取一個"像樣的住所"的人,不知道怎樣會想到了一個主意,用他自己認為一定會成為一種絕對新穎與適當的形式,來歌頌人類和美國。所有他的各種愛好和經驗部獲得發展:母方的教友會思想;莎士比亞與歌劇─在公共場所聽到唱說其辭句後心裏的興奮;使他對於自己的性情感到安心的骨相學;遠比骨相學體面的其他科學,在這方面他和愛默生有點相似,從裏面找到了宇宙的哲理;馬丁‧塔珀流動的詩體;喬治‧桑的小說《康素愛蘿》(Consuelo) 及其續篇《魯城的伯爵夫人》(the Countess of Rudolstadt),這可能和他自命為人類的發言人有點關係;愛倫.坡,他向他指出長詩的無當;百老匯的人群,或是布魯克林渡船上的人群;從大西洋上湧來的浪潮;鄉間可愛的季節變換;大陸的遼闊,從他居住的地方一直向西海岸不斷延展:所有這些以及許多別的東西,他全寫進一八五五年他三十六歲那年七月間在紐約出版的初版《草葉集》中了。它收集了十二首詩,其中份量最重的是《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 序文(惠特曼的散文和他的話極其類似)和詩一樣,堅持類似愛默生闡明的真理:平常人的神聖,和他們神奇的循環不已的形形色色的生活。不過它們的風味完全和愛默生的不同。後來經過修正、增補、迭次出版的《草葉集》也是一樣。不錯,它們是表現了愛默生似的自滿,特別是在最初幾版裏。可是表現的方式並不相同:有時聲音比較粗糙,有時語氣又過分歡樂,幾乎和愛默生冷冰冰的說教,同樣使人生厭,然而在感覺上給你一種熱情,使你不能對它置之不理。惠特曼最好的詩篇遠比愛默生的燦爛:惠特曼某些謝句裏有一種早晨的欣悅,愛默生就沒有能夠把它注入自己的詩篇:
看那東方的破曉!
些微的光使無邊的疏稀的黑暗漸漸消失,
空氣的味道很好。……
我聽見鳥在聒噪,麥在習習搖風,火舌低話,樹枝畢剝著燒我的早餐。……
我在街上走、我在河上過、看到和聽到的最小的東西上都掛著晶瑩如珠的光華──
誰能抗拒這樣的詩句,還去斤斤計較這能不能稱為詩? 這樣的句子,我們覺得惠特曼說得不錯,正是"分得平均的豐餐,這正是可以療饑的肉食"。
即使我們同意說這些詩的寓意沒有霍桑的深刻(雖然事實上並非如此),這一類的詩也只是惠特曼的一個方面。馬克斯‧比爾的漫畫中的滑稽的惠持曼改了樣子,變得微妙起來了。然而就是在最初幾版裏,他也遠不如攻擊他的人所說的那樣喧囂。他是有一點落落寡合,"不論在局內,還是在局外"。在他那個時代,有些批評家說他最喜歡宣揚家醜,果真如此,他又顯得過於躲躲閃閃了。"暗示"這個詞,他說最足以說明他的詩情,在他的待裏,"每一句每一節都有往往在表面上看不到的內蘊。"可能因為他本能上想遮掩他的同性戀傾向,某些地方顯得有些晦澀;無論如何,這和傳說中外傾性格的惠特曼並無關係。試看下面這些奇異而可愛的詩句:
永遠是堅實的不沈的土地,
永遠是吃的吃,喝的喝,永遠是日出口落,依然是大氣和不停的潮汐,
永遠是我和我的鄰人,爽快、邪惡、真實,
水遠是古老的不能解釋的問題,水遠是那刺痛的拇指,是那心癢和渴望的氣息,
永遠是使人厭煩的梟鳴!梟鳴!直到我們找到那陰險的傢夥藏身的地方,揪他出來,
永遠是愛,水遠是生命啜泣的淚水,
永遠是額下的繃帶,永遠是死的抬架。
我們可以從《自我之歌》中找到五十節諸如此類使人迷惑的詩句。他也沒有在這首詩裏,或者在他的全部作品裏,堅持說世上沒有不公道與痛苦。他說:"痛苦是我換洗一次衣服。"他也會痛詆他的祖國:
除了讓你想到苦役以外不能想到別的!
誰也不能朝著他的目標前進!
─ ─ ─ ─
讓日月去罷! 讓風景接受觀眾的歡呼! 讓星辰之下只有冷漠!
上面這幾行詩摘自《回答》('Respondez!'),這首詩在以後幾次出版的《草葉集》裏被他刪去了,但是這首詩裏所表現的憤怒和沮喪,也可以在別的詩篇和《民主遠景》裏找到。
不過,沮喪並不是惠特曼主要的詩情。把喜樂分散在人生 "爽快、邪惡、真實" 的特性裏,這才是他對於死後求取永生的看法:
極小的嫩芽表明世間其實並沒有死,
即使有死,它也導致了生,而且並非到了最後死亡才終結,
一有生命,死亡就終結了。
─ ─ ─ ─
什麼東西都走向前,走向外,生生不息,
死並不是想像中的那個樣子,而要幸福些。
惠特曼年事漸長,越來越想到死的問題──不過他認為死只是一個生命與另外一個生命之間的插曲。對他而言,死亡沒有痛苦,說真的,他在十分年輕時已開始向生命告別了。他在四十幾歲寫的那首《裹傷者》裏,就曾說過:
像個彎腰的老人,我來到新的面孔之間。
說不定是內戰中那一段醫院生活,加速了這個進程。正像一位希臘史家所說的,平時父死子葬,戰時子死父埋。在當時的美國作家裏,只有惠特曼與梅爾維爾充分瞭解內戰的悲慘意義。他覺得自己是個父親,當他看見整個美國,在飽嘗戰場上的苦難之後,躺在外科醫生的刀下,他把他的感情宣洩在淒惋而莊嚴的詩句裏:
話最重要,像天空那樣美,
美到戰爭和所有殺戮行為到時都已完全消滅,
死亡與黑夜一對姊妹的手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輕輕洗揉這個污穢的世界。
同樣寧靜的爐火純青的意境,也表現在他悼念林肯之死那首偉大的《上次丁香在門前庭園盛開的時候》裏。
惠特曼在一八五五年版《草葉集》的序文裏寫道:"在所有人類之中,偉大的詩人是心氣平和的人。"這句話在《藍色的安大略湖濱》又出現過一次;心氣平和最足以總括惠特曼特別的性情。他覺得驕傲之中可以、也應該帶有謙遜。民主的地位最為崇高,但是在惠特曼的詩中是以自然界中最卑微的草來象徵的;他心日中的新人,說的是"草一般簡單的話"。他認為,說人生一如古典建築那樣精確,是子虛烏有的事;它毋寧像自然界的一個物體:自有其有機組成,不過形式是意想不到的,不對稱的,甚至是任性的。他在一次關於劇作《阿伯拉罕‧林肯之死》的講演中說:
主要的事件,謀殺的發生,就像任何最平常的事件那樣平靜,那樣簡單,比如說植物生長時蓓蕾或是豆莢的進發。
他在這裏一點都沒有咆哮──在那樣的場合有多少人能夠不咆哮呢?──他解釋那個事件有如講解自己的詩,"在詩裏,事情的發生,一如在自然界中,好像沒有照顧到部分,也沒有特殊的目標"。他還在另外一個地方談到他自已的時候說,詩人把"他的韻律和均一藏在詩的根底,本身是看不見的,而是像花叢中的丁香一簇簇四處怒放,終於結為渾成一體的東西,如西瓜、栗子或梨。"他對於和他同時代的詩人缺乏自發性和真實的敏感,感到惋惜,例如對坦尼森的詩:
英國社會生活的氣息……像一種看不見的氣味瀰漫在篇頁之間:那種懶散、傳統、奇癖、莊嚴的無聊;愛的飢渴,就像深藏不露的脊髓;….古老的房屋和傢俱……到處是發了黴的秘密;那些青青的草木、牆上的長春籐、壕溝、英國戶外的風光,窗子裏面曬著太陽嗡嗡作聲的蒼蠅。
我們從他這段批評詩無生氣的精采論述中,可以看出惠特曼對於詩人的看法,他認為詩人不應該像"法官斷案那樣來看待事物,而是應該像太陽之臨照軟弱無力的東西"。
像任何一個詩人討論詩人作用的理論,惠特曼的看法也只是他個人的看法。但是他這個看法傳播得比較廣。我們可以同意惠特曼的批評者的說法,如果他鼓勵未來的美國詩人完全依靠發狂似的詩人的直覺,接受他的忠告是有危險的。在他大談詩人,比如說他在新舊世界之間提出對比,極力歌頌拓荒者,或是假定普通美國人將一致起來歡迎他們 "聲嘶力竭的講演者" 時,必然最不受歡迎。他筆下那種朋友和同志的美國可能讓人看了有點難為情;說來真有點諷刺意味,目前他的詩篇裏面最為大眾所熟知的一首詩,反而是那篇完全守舊的《哦船長!我的船長》('O Captain! My Captain!)。不過,假如說他的最"大眾化"的詩是他最弱的詩,他曾竭力向群眾呼籲,那倒是典型的美國作風,一點都不錯。他在這一方面的失敗並沒使他感到難過。假如一個詩人不能向人類說話,他至少可以為人類說話(如果他做得好的話);這正是惠特曼所做的,而且做得非常出色。